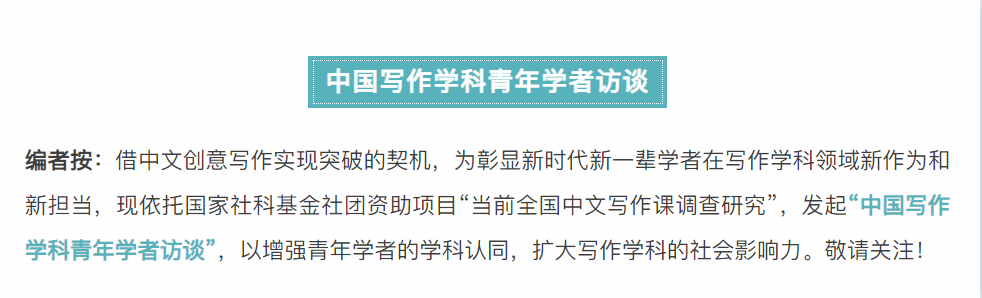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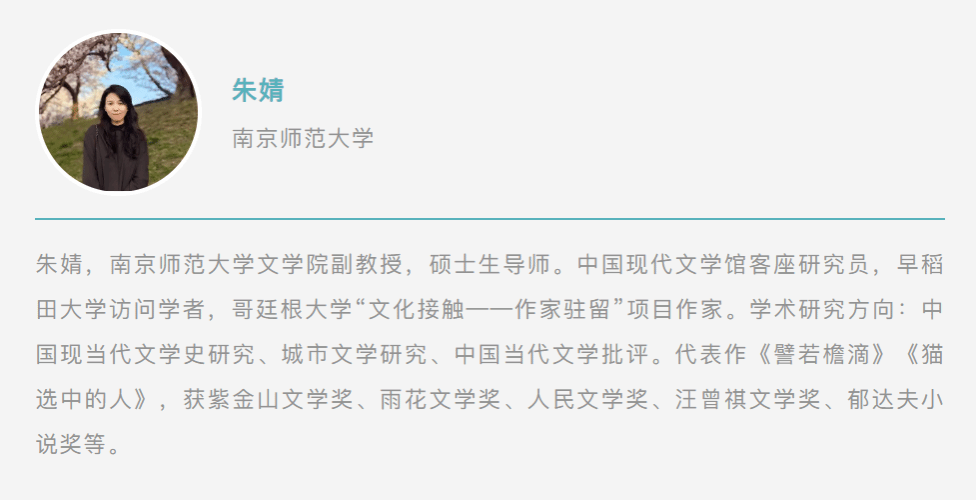
01
您如何与写作学科结下不解之缘?请您介绍一下自身学习和研究写作学科的经历。
我2000年到2004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2004年到2007年在南京大学读戏剧戏曲专业研究生。2008年2月到6月,在鲁迅网赌
参加第八届作家高研班。2008年9月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写作学教研室任教,由此进入写作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期间获得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文学博士学位。
和写作学科的另一层联系,还和我个人的创作经历有关。我自2003年本科三年级开始文学创作,主要的文体是短篇小说。2004年1月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早期写作,也就是在2004到2007年之间,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长篇小说。这个阶段,也就是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有一个持续给期刊写稿,不断发表和出版的过程。因此,硕士毕业后,进入了鲁迅网赌
第八届作家高级研修班学习。
也是因为这样的创作背景,2008年5月,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写作学教研室希望能够招募一位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同时又能够创作的老师,由此我获得了入职南师大的机会。南师大一直有比较深厚的写作传统,是国内较早聘任作家教授写作课程的大学。我所在的写作教研室就有作家鲁羊和郭平,他们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在南师大任教了。相较于其他高校,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教育始终保持着两大特色:其一,通过独立设置的写作教研室持续完善写作课程体系;其二,在师资引进和培养中坚持“双能型”标准,创作能力与教学能力并重。这种对写作教育的系统性建构,正是我当年得以进入该领域从事教学研究的重要契机。

朱婧(左二)参加思南书局活动
02
您硕士阶段对戏剧戏曲的研究对后来的研究和创作有什么影响?
从研究方面来讲,2017年,我立项完成了江苏省文化厅一般项目“优质类型电影研究与国产小妞电影”(聚焦于女性,即国外的chick flick,也被译为“小鸡电影”)。2021年,我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做的是现代都市及其催生的文化与文学。我的研究兴趣从“小妞电影”转向城市文化和文学,不变的是对都市里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不同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后来做研究和写作时,这些积累帮我更好地观察消费社会对女性生活、心理的影响,也让我在女性写作领域里不断对照传统、寻找自己的思考方向,算是保持研究连贯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从创作素材角度而言,基于硕士阶段的戏剧戏曲学专业背景,写小说时把戏曲元素揉进故事里就变得顺理成章。像去年刚发表的短篇《思凡》,就是直接把传统折子戏的结构打散了,重新嵌进现代都市的叙事里——可能潜意识里那些科班训练总在影响我的创作方式。
03
您在日本和德国的访学经历对您的创作和研究有什么影响?您认为日本和德国的写作学科与中国的相比有什么特色?
在日本访学和德国驻留期间,我从事的具体工作并不是跟写作学科紧密相关,但是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2019年2月到2020年2月在早稻田大学访学期间,我的合作导师是千野拓政老师,我们的合作课题是“东亚青年亚文化与青年写作”。 我早期写作出发的《萌芽》杂志和80后写作群体正是这个项目重要的观察对象。我在千野拓政的办公室收集的整箱的世纪初的《萌芽》杂志中看到我自己的作品,实有所动。东京访学对我个人写作影响是,有感于林文月先生的京都访学对她的学术以及创作的转折性意味,我于2019年4月写了一篇论文《越境者的文学景观——观察台湾作家林文月的一个角度》,梳理林文月先生个人写作史的演变,这篇文章后来发表于《扬子江评论》。后来我又用她的经历写成小说《先生,先生》,2020年1月发表在《花城》杂志,小说的主题是中文系的薪火相传。
可以说东京访学那一年,让我第一次跳出具体研究,整体审视自己的学术与创作路径。特别是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切换问题——这种思考或许能为当下创意写作学科面临的普遍困境提供参照:青年作者如何在学院体制中既保持创作活力,又能建立学术话语。关于写作本身,当时我写了一系列关于书店或其他主题的散文,这些看似零散的记录,后来都成了理解创作本质的珍贵切片。双重身份的体验,让我更理解创意写作学科在学术与创作间的独特定位。
2024年6、7月,因为南京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哥德学院的“文化接触——作家驻留”项目,我在哥廷根大学驻留了一个多月。期间,除了完成哥廷根大学的工作,我还以博物馆为中心,去了德国跟其他的几个欧洲国家旅行,观览了柏林国家美术馆、柏林画廊、荷兰国立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巴塞尔美术馆、卢浮宫、奥赛博物馆等。那是一场不算长的欧洲艺术之旅。对我的直接启发是,2024年8月,在广州花城出版社主办的李娟作品研讨会上,我借用16至17世纪尼德兰风景画中的大风景(landschap)与小风景(gezicht)概念分野,来观察李娟散文的取景方式。顺着这个思路我写了篇论文,现在正处于修订完善与终稿准备阶段。2024年6月在柏林旧国家美术馆参观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无限风景”特展的经历,构成了我观察风景的核心启发——那些宏大场景中个体所体验的崇高与孤独的共生状态。我以这段身体旅行为切入点,试图说明访学经历不仅关乎文化身份的转换,更在文学与艺术的交汇中,以具体而私密的方式持续影响着研究与创作的双重实践。
至于德国驻留对我个人创作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当时我在哥廷根大学的Barbara Dengel老师安排下与德国作家达妮埃拉-德洛舍尔(Daniela Dröscher 1966-)做了对谈和交流,我们共同关注着家庭与时代,女性的现实处境等问题。达妮埃拉-德洛舍尔2024年出版的小说《关于我母亲的谎言》,就是以孩子的视角展开对婚姻和母亲的观察。在2024年7月8日对谈的晚上,我引用了杜拉斯在《物质生活》中的一句话,“女人布置房子是一处乌托邦。她忍不住要这样做,不是用幸福本身,而是用对幸福的求索,去吸引自己最切近最亲爱的人。”然后,达妮埃拉表示,这也是她最喜欢的文章。对我们来说,去观察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幽暗,很难说起点是因为不满,可能是因为更强烈的信念。对谈的时候,我被提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题——我如何看待女性和身体的关系,以及在中国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因为在达妮埃拉的小说《关于我母亲的谎言》中,塑造的母亲形象,其社会可见性仅局限于肥胖的体型表征,而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诉求与生存困境则始终处于公共视域的盲区。她也指出,太胖这个判断,是对于母亲的谎言。2024年夏天,小说改编的话剧在德国几个城市巡演。话剧的预告片中有两句话,一句是“儿时我认为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另外一句是“我为我的妈妈感到羞耻,我用父亲的眼光在审视我的妈妈”。我就会想,“妈妈”是否从最美丽的女人变成让“我”感到羞耻的女人,关键在于女性看待和对待自己身体的方式,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和愉快,还是在用他人的眼光审视和提出要求。如此,我就想到了女性跟身体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认为只有当女性有权利去定义和决定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才有可能会获得身体自由。而这种自由不仅仅关乎美丽与尊严,还关乎健康与生存。由此,我就写了我想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小说《当我绽放时》,今年三月在《人民文学》发表。

朱婧(右一)在哥廷根大学的文学交流
04
您在写作学科的主要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是什么?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其实我在创意写作领域的学术成果还比较有限。目前主要的成果是2020年8月在《写作》杂志发表的《经验的转换和安置——基于创意写作实践的过程性观察》,同时在2020年的第7期的《中华文学选刊》,参与了一个类似于访谈式的文章,名字是《创意写作:经验的转换和安置》。这篇论文后来被收进复旦大学张怡微老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写作知识的革新》论文集,并获评中国写作学会《写作》杂志首届优秀论文奖。说来惭愧,这应该算是我在这个领域目前最重要的探索了。
论文将创意写作课程的教与学的视为有机整体,关注作家经验和写作知识的转化机制,借由杜威“一次经验”理论(意指一次完整的、圆满的经验。“一次经验”,同时意味着真正反思的时刻,这种反思会影响下一次类似的行动),以此来阐释作家驻校——创作经验形成的写作知识——学生获取知识进行写作实践——形成完整的自我经验。从前者的“经验”到后者的“经验”,关乎如何提炼出知识(有效的、规律的、可执行的内容)。每一次经验,都是反思和行动的结合,这一点用在创写课堂上,即可陈述创意写作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05
您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其实和我作博士论文时期具有延续性关系。我对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的探索,近阶段集中在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文化和文学上,这跟写作学的关系可能会有点远。另外,我去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客座研究员,根据项目安排,每隔一两个月会有一次主题性学术会议。所以去年基本上还是在既定的主题范围内,关注了一些现当代文学现场的问题,当然也根据个人的观察和兴味写作了一些论文。
一般来讲,就是把论文写出来以后,先对论文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评估,然后再去联系合适的刊物。这个评估包括论文的选题形式,是作家作品论,还是综合性的文章;整体形式是更接近于学术论文,还是更接近于文学批评,这样有利于选择相对合适的刊物,这些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06
在写作领域有哪些论文著作或者教材对您影响最大?对您影响较大的代表性学者有哪些?他们的研究对您的启发是什么?
写作领域我们是没有用教材的,我们的写作课程基本上是以专题的形式在推进,可能不同的课程跟不同老师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点联系更紧密。因此,对我的写作教学影响更多的,可能是我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跟我个人的阅读会更密切一点,变化比较多。
当然在写作课程上也有一些具体的、基础的参考书,我每年都会跟同学推荐,比如说作为细读的标杆的王安忆老师的《小说课堂》,毕飞宇老师的《小说课》,格非老师的《文学的邀约》。回到刚刚谈论的阅读、撰写论文的心得体会的问题,我认为通过这些著作能够有效地提取作家经验,传达给学生。如果学生能够接触到这样一种从作家经验中提炼的知识,然后由此去通过个人的创作活动来消化、生成自己新的写作认识的话,就是我认为的非常理想的创意写作的教育过程。这几位老师,可以说是跟文学创作活动过以及写作课程关系密切,都在有影响力的高校从事写作相关课程的教学活动。这几本书是我会推荐给创意写作课的同学们看的。
07
您现在主要上什么写作课?这些课程的收获是什么?有什么存在的困难?
我现在教的主要课程是写作训练、小说创作、文学评论写作、艺术感觉与审美批评,之前还承担一些影视相关的课程,包括电影社会学、影视文化产业学等。收获就是,因为我们教授写作的课程,一直都要跟学生一起研读有价值的经典作品,并且一直在关注文学现场,所以让我一直保持对于现场的关注,进而能够反复在这种阅读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困难则是,学生的阅读时间比较少。

朱婧《猫选中的人》书影
08
您在论文中提到:“作家进入创意写作课程,在课堂主导上显著的特点即是‘像作家一样去阅读’的方式的引导。”请您结合教学经验谈谈。
我们为新媒体与创意写作方向的专硕提供作家进入课堂和改稿的实践。我们开设了创意写作实践系列讲座,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就创意写作问题来跟学生进行交流。我们邀请过格非、毕飞宇、徐则臣、鲁敏、索南才让、曹寇等前来授课。我们还会跟期刊合作举办改稿会的实践活动。我们和《青春》杂志社毕飞宇工作室合作举办了“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以改稿会、研讨会的形式,培养学生专业化写作能力。我们还与《萌芽》杂志社合作举办《萌芽》见面会,发现和培养青年写作者。
在既针对研究生,也针对本科生的小说创作课程中,我们每年开设专题——“文学的阅读”,就是希望帮助学生有智力和知识能力去解读,同时也有感受力去理解文本。我们通过分主题阅读的工作坊共同阅读和讨论。比如说,我们开设过“出走母亲的焦虑”主题阅读活动,读门罗的作品《漂流到日本》和《沙砾》。我们还开设过一个叫“纪实与虚构”的工作坊,一起研读了法国作家、批评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作品《永恒的孩子》和《然而》。这两部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自撰式”写作。福雷斯特因他个人的失去女儿的真实经历写作,而批评家的身份帮助福雷斯特有一个先验的认识,提供了一种从经验出发,以文学方式处理经验的清晰的模式,所以作为学习的对象是相当合适的。当然他也处理了关于如何面对伤痛的问题,女儿死亡的事件,在福雷斯特的自述中是他个人的故事,但同时又通过跟他人的经验的连接,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故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这个故事出发,写出了不同的文本,从同一个故事讲出了许多其他的故事。这个方式是我们当时在引导同学们细读作品时候所关注的,非常适于初写作者,因为初写作者往往会想要去处理个人的经验。
从主题的延伸来讲,因为福雷斯特处理的是一个关于丧失的题材,所以在读福雷斯特的时候,我们也让学生读了非虚构作家琼·狄迪恩的《奇想之年》和《蓝夜》,它们是琼·狄迪恩以失去丈夫和女儿的经历写出的作品。我们注意到主题的切近,也注意到方法的切近,然后在同样的主题和方法里面,让学生读有关联的文本群。这可谓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朱婧(前排右五)参与的文学之都公共文学课
09
您平时写作习惯是怎样的?有没有哪部作品的创作经历令您印象深刻?
我一般会确定要写作的主题,然后寻找一个合适的形式。比如说我这几年持续写关于丧失的主题,我的方法就是在文学史当中寻找关于丧失的主题的回应,然后想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主题。比如我刚刚讲了,我跟学生研读了一系列的关于丧失的文本,福雷斯特的文本、琼·狄迪恩的文本,这也是我个人关注的一个向度。但怎么去处理它呢?我自己是把理解时间和记忆作为一个处理的方法。简单来说,是要通过重新描述记忆,赋予曾经的生命经验新的位置形式和秩序,去理解那种生命中失去的部分,由此理解丧失是怎样的事实。
这里面用到的其实是A·S·拜厄特在《记忆与小说的构成》中指出的,人类不同于(绝大多数)其他生物,因为我们能够在记忆中形成曾经存在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的形象,并且能够用这些形象创造我们的一个连续的自我观念,一种由连贯的记忆形象组成的自我意识。因此,在我的小说中,女性主人公往往是通过重新描述自己的世界而变成“真正的”自我,而这一种描述的成功与否,关系回忆的形式和生命真相的距离。它需要综合有意味的记忆、认识和顿悟,从而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学形式。这就是通过处理记忆来去处理伤痛的主题吧,也是我一般的创作方法,就是先寻找主题,然后寻找合适的方法。近几年,我的小说《鹳》《吃东西的女人》都用了这样的创作形式。
10
您近年来的作品与早期的作品风格差异较大,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我的小说创作中断过一段时间,从2008年到2018年中断了有十年。十年之后再回到文学现场,已经有很多变化,文学的审美趣味和风尚、文学的生态格局都在变化。当然我个人的日常生活、心智、文学趣味也发生了变化。我以个人的十年之变回到了变化的文学现场,那转变自然是发生的。
另一方面来讲,这十年期间,我读完了博士学位,我自己所关注的当下的城市文化和文学,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不断改写当下社会的经济格局和社会分层,我也试图通过阅读和写作理解消费社会的逻辑对不同阶层的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以及我们时代的女性观如何形成。我的写作关心女性的具体处境,在女性写作的传统寻找回应和位置。
如果在文学史观察,我这几年的小说关注“家庭中的女性”,她们或是“主妇”或是“妻子”,都可以汇流“家中天使”的文学脉络。因此,应该讲是知识的准备,个人的经历和文学现场的变化共同引导了我的创作转变的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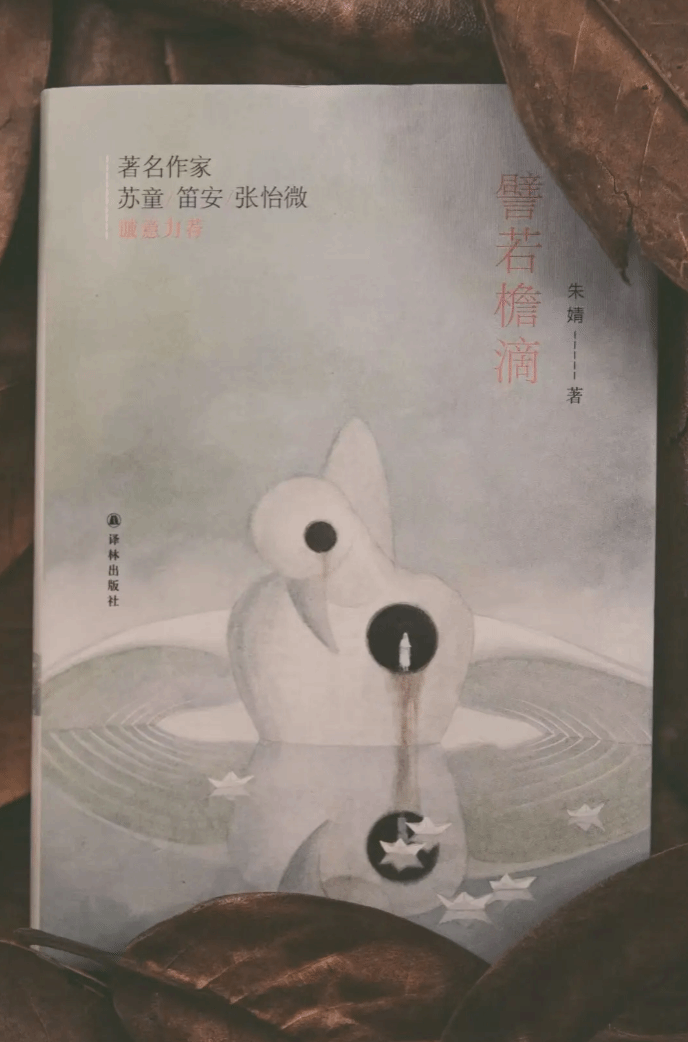
朱婧《譬若檐滴》书影
11
您认为小说写作和论文写作有什么异同?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写作方法?
写作的前提构成很复杂,也存在各种类型的作家。学术修养可能对某种类型写作很重要,比如说学术随笔或学者散文。但是靠知识可能成为学者,却不一定能够成为作家。对于作家来讲,如果写作中需要某些知识,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许多作家的写作实践中都有田野调查和史料检索。当然,当下大学场域中的作家群体构成是较为复杂的,凭借学术积淀或知识储备进行创作同样可能成就优秀作家。例如王尧教授的《民谣》,其创作动力更多源自个人生命经验而非系统性的学术积累;而李洱的《应物兄》则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作为叙事根基。他们都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们所征用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许多作家写作的时候,比如迟子建为创作《伪满洲国》和《白雪乌鸦》,做了充分的知识调查。而在更年轻的作家中,这种意识可能更强烈。譬如葛亮创作《北鸢》时,其历时三年的文献考据工作便印证了当代写作场域中资料工作与创作活动之间复杂的构成性关联。
如果说文学创作的核心在于感性形象的塑造,而学术研究需要诉诸理性逻辑,这种分野在高校作家群体中尤为明显——他们既需要切换到学术研究的语言状态,又需在创作时激活另一套思维模式。但二者并非割裂:在推崇理性与知识的时代,仅凭感性已难以支撑深度的文学探索。学术训练带来的逻辑思维(如谋篇布局能力、田野调查方法)确实能为小说创作提供支撑;而文学感性所蕴含的自由特质,始终是文学自我革新的原动力,既能突破理性的遮蔽拓宽认知维度,又能催生新的可能性。两者虽路径不同,但无论是论文写作还是小说创作,本质上都是思维模式转换的具体实践。
12
就您个人的研究和写作经验而言,您如何看待地域文化与写作之间的联系?
2020年1月,《花城》策划了城市文学专题,计划为每个城市邀请一位作家创作在地性作品。所以彼时我要着手思考如何书写南京这座城市。我并不是南京本地人,当然我在南京已经生活了很久,2000年来这里读书,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后来我逐渐明确,可以通过追溯中国现代大学在南京的发展史,来观察高等教育机构对城市文化气质的形塑过程。为此,我选取了若干历史地标作为考察对象:以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为核心,辐射周边的民国建筑群及颐和路片区,特别关注连接随园与南大鼓楼校区的陶谷新村——这条承载着学术文脉的道路,最终成为我书写南京的叙事枢纽。这个案例体现了我将特定城市空间的文化解码作为文学创作基点的实践路径。
13
您既是作家,又是学者、老师,这三重身份如何相互影响?
现代以来,大学是一个相对自由且适合写作的场所。在学院从事写作,特别是教授文学课程时,必然需要研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作家的创作成果,这种学术积累既为个人写作提供了参照体系,也在选择阐释对象的过程中,促使我们反思历代作家的写作范式。例如我近年作品中对家庭女性的观察,正是通过在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发现的母题探索路径。
我曾从19世纪英国诗人帕特莫尔的长篇抒情诗《房间里的天使》和伍尔夫《给女性的职业》中,梳理出“家中天使”的形象,勘察这一类维多利亚时期理想女性是如何在后续的文学作品如A·S·拜厄特的《占有》《婚姻天使》等作品中一再出现,然后为我个人的创作寻找到文学谱系上的呼应,由此对自己写作的意义做出一种确认。
对我来说,做学术研究跟文学创作,是需要切换不同的工作状态的,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且有效地调整思维状态和语言状态。研究工作和创作工作有机结合对我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工作方法。比如,通过对林文月学者-译者-作家“三支笔”(三位一体)写作模式的研究,我试图建构一种适配自己身份定位的复合型工作范式——这种既能维系研究严谨性又保持创作活力的方法论,本质上是对当代人文学者如何平衡知识生产与艺术实践这一核心命题的实践回应。
这几年,我关注女性写作,进行相关的创作和研究,希望这些工作之间能够相辅相成。而且有的时候,关注和思考的内容,用一种工作形式不能完全表达,在另外的工作形式中能加以补充。同样以林文月为例子,写完对她的研究论文之后,我会以此为起点写一篇小说,这是一个例子。去年,我关注明清时期特定阶层的女性的结社和创作活动,写作了关于明末清初女词人徐灿的研究性随笔,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创作了小说。
由于我教授写作与文学批评课程,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往往会倾向那些能引发内心共鸣与审美共振的创作主体。比如除林文月外,我也持续关注复旦大学张怡微老师的文学创作,并撰写相关评论文章。
在博士论文阶段,我选择以重审“上海摩登”为切入点,由此聚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这一研究路径的形成亦与我对王安忆作品的阅读密切相关。王安忆在大学的教学、写作以及对于其他作家作品的解读启发了我,因此我也选择王安忆作为我观察“上海摩登”的一个样本。所以说,阅读和关注会让我选择一些更合适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并让其进入到我的教学过程,最后可能又参与到我的创作活动中。
14
在教学和研究之外,您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您是怎样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如何评价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
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目前来讲,能够让工作相对流畅和持续地展开就已经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了。我的兴趣爱好就是我的工作,因为阅读占了几乎大部分的时间吧,那应该也算是一种兴趣。比如说很多时候读的东西,肯定是因为这个阶段我觉得它有兴味,而它最后其实也变成了我的工作内容,或者说启发某些创作,所以基本上兴趣跟工作是联系比较密切的。
15
对写作学科的学生以及年轻一代,您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化了,文学的新变一定会产生的。当然每个时代都有一部分的青年作者,他们愿意当文学的守成者。新作家旧文学是常态。他们依然会遵循、尊重,当然也试图欣赏一种写作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有一些青年写作者,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青年文化,在他们的写作中是扑面而来的。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城市化、以及网络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带来的是青年作者生活的新世界,也是他们文学的取景框。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写作,不仅要去绘制新的生活图景,而且要去探索文学的新方法或者路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果能够完成独属于他们的审美创造,也是真正地回应了自己所在的时代吧。
